敦煌万亩盐碱地变“希望田”
敦煌万亩盐碱地变“希望田”
敦煌万亩盐碱地变“希望田”——陇原湿地(shīdì)观鸟手记
5月22日是(shì)国际生物多样(duōyàng)性日,今年活动的主题是“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”,呼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(zhīdào),创和美永续之路。甘肃(gānsù)的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,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、物种和遗传多样性。本期我们和您一起去甘肃湿地,追寻飞鸟划过(huáguò)的痕迹,感悟自然生态之美。且让我们暂卸都市生活的“铠甲”,让瞳孔(tóngkǒng)重新校准焦距——在羽翼划破天际的弧线里,重拾对这颗蓝色星球的景仰与热忱。
近来,观鸟这一活动愈发受到关注,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(huàtí)。“观鸟热”的兴起,更多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(gòngchǔ),以及人们对于自然生态(zìránshēngtài)之美的感悟与欣赏。
甘肃,这个被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内蒙古高原共同托举的(de)观鸟秘境,既是(shì)候鸟(hòuniǎo)迁徙的十字路口(shízìlùkǒu),亦是现代人重拾自然诗学的殿堂。观鸟人的长焦镜头里,甘肃湿地是四季轮转间永恒的惊叹号。这里所见的绝非仅仅是物种名录与迁徙数据,而是一场横跨四季的生命史诗。在这片土地(tǔdì)上,藏着祁连山雪线融化的秘密,藏着盐池湾灰雁振翅的节奏,藏着尕海湖(hú)晨雾中鹤舞的韵律,藏着黑河黑鹳群留在大地的墨绘,也藏着三江口(sānjiāngkǒu)大天鹅玉翅上未干的霜露……
 盐池湾湿地的斑头雁(bāntóuyàn)。
春之迁徙:盐池湾的候鸟交响曲(jiāoxiǎngqǔ)
当祁连山(qíliánshān)的(de)(de)雪线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后退时(shí),盐池湾的冰封镜面开始出现裂纹。最先感知到这一(yī)变化的不是融水冲刷出的沟壑,而是斑头雁黄色的喙。它们在三月底的晨昏线上划过,双翅呼呼(hūhū)生风。冰凌碎屑尚未与(yǔ)雁羽摩擦,便已发出细密(xìmì)的簌响,像是古琴开弦前的调音。野马南山与党河南山两山之间形成的盆地内河流纵横、湖泊密布,草甸、沼泽交错,是斑头雁和其他水鸟世代栖息繁衍的场所。尽管先头部队在3月下旬就已抵达(dǐdá)这里,主力部队却要到4月上旬才会姗姗来迟。此时斑头雁幼体已在越冬地充分发育,羽衣上几乎看不到如苔藓般斑驳生长的新羽,只是头部的两条黑(hēi)带不如父母深邃,这是它们少经风霜的证明。它们降落在湿地滩涂时,雝(yōng)雝鸣雁,那声音或许与两千年前苏武牧羊时在北海之畔听到的有些许相似。
大鵟在峡谷热流中绘制(huìzhì)着无形的几何图案,棕(zōng)褐色的双翅带着几朵白色和一抹铁灰,如它的性格一般刚毅。作为留鸟,它兴奋地(dì)扫视着一年一度的迁徙来客。祖传的巢穴以猎物(lièwù)的骨殖搭建在断崖旁边,日积月累,被反复利用。当它俯冲时,影子在岩壁掠过,如同某种远古图腾(túténg)在苏醒。再次飞起的刹那,它明黄色(huángsè)的爪间已然擒着不知哪只早起的倒霉旱獭。
候鸟的(de)迁徙是(shì)写在基因里(lǐ)的史诗。蓑羽鹤是春天的迟到者,但同样也在践行某种生命对时空的承诺。当它们(tāmen)终于如柳絮飘落般降落在盐碱滩时,鸣叫里似乎藏着整个迁徙季的疲惫与喜悦。即便它们只是在空中飞过,也是震撼人心的画卷。我曾在瓜州某无名山巅,偶得瞥见头顶掠过的蓑羽鹤阵,刹那间我产生(chǎnshēng)了错觉(cuòjué),看到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卸下了璎珞。
雄性凤头潜鸭的黑色头羽在春光下泛着紫金光泽,虽名为“凤头”,冠羽却(què)不似戴胜那样张扬,也不比普通秋沙鸭那般不羁,而是像一条耷在头后的小辫。它的配偶(pèiǒu)发色(fāsè)棕褐,小辫更为收敛,却也同样俏皮(qiàopí)。它们为了几条小鱼小虾而频频潜水,潜入水底时尾羽灵如(língrú)船舵,搅动的水草间偶尔露出一抹光影。
同样被冠以“凤头”,凤头麦鸡的个头比凤头潜鸭小得多,发型却(què)向上竖起,极具个性。它草黄的眉纹和白色的腹部在晨光中分外显眼,翅上绿、紫(zǐ)、蓝色的金属光泽更是交错闪耀。它的小脚爪在水畔一冲一停,求偶叫声如哀怨的呜咽,却在这旷野之地(zhīdì)奏出缠绵的乐章(yuèzhāng)。
【春思】候鸟用迁徙适应季节变换,正如人类用篝火(gōuhuǒ)抵御寒夜。当灰雁和蓑羽鹤穿越死亡谷时(gǔshí),我们(wǒmen)正在地铁里为迟到焦虑——或许所有生命都在穿越各自的险峰,只是海拔标注的单位不同。
盐池湾湿地的斑头雁(bāntóuyàn)。
春之迁徙:盐池湾的候鸟交响曲(jiāoxiǎngqǔ)
当祁连山(qíliánshān)的(de)(de)雪线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后退时(shí),盐池湾的冰封镜面开始出现裂纹。最先感知到这一(yī)变化的不是融水冲刷出的沟壑,而是斑头雁黄色的喙。它们在三月底的晨昏线上划过,双翅呼呼(hūhū)生风。冰凌碎屑尚未与(yǔ)雁羽摩擦,便已发出细密(xìmì)的簌响,像是古琴开弦前的调音。野马南山与党河南山两山之间形成的盆地内河流纵横、湖泊密布,草甸、沼泽交错,是斑头雁和其他水鸟世代栖息繁衍的场所。尽管先头部队在3月下旬就已抵达(dǐdá)这里,主力部队却要到4月上旬才会姗姗来迟。此时斑头雁幼体已在越冬地充分发育,羽衣上几乎看不到如苔藓般斑驳生长的新羽,只是头部的两条黑(hēi)带不如父母深邃,这是它们少经风霜的证明。它们降落在湿地滩涂时,雝(yōng)雝鸣雁,那声音或许与两千年前苏武牧羊时在北海之畔听到的有些许相似。
大鵟在峡谷热流中绘制(huìzhì)着无形的几何图案,棕(zōng)褐色的双翅带着几朵白色和一抹铁灰,如它的性格一般刚毅。作为留鸟,它兴奋地(dì)扫视着一年一度的迁徙来客。祖传的巢穴以猎物(lièwù)的骨殖搭建在断崖旁边,日积月累,被反复利用。当它俯冲时,影子在岩壁掠过,如同某种远古图腾(túténg)在苏醒。再次飞起的刹那,它明黄色(huángsè)的爪间已然擒着不知哪只早起的倒霉旱獭。
候鸟的(de)迁徙是(shì)写在基因里(lǐ)的史诗。蓑羽鹤是春天的迟到者,但同样也在践行某种生命对时空的承诺。当它们(tāmen)终于如柳絮飘落般降落在盐碱滩时,鸣叫里似乎藏着整个迁徙季的疲惫与喜悦。即便它们只是在空中飞过,也是震撼人心的画卷。我曾在瓜州某无名山巅,偶得瞥见头顶掠过的蓑羽鹤阵,刹那间我产生(chǎnshēng)了错觉(cuòjué),看到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卸下了璎珞。
雄性凤头潜鸭的黑色头羽在春光下泛着紫金光泽,虽名为“凤头”,冠羽却(què)不似戴胜那样张扬,也不比普通秋沙鸭那般不羁,而是像一条耷在头后的小辫。它的配偶(pèiǒu)发色(fāsè)棕褐,小辫更为收敛,却也同样俏皮(qiàopí)。它们为了几条小鱼小虾而频频潜水,潜入水底时尾羽灵如(língrú)船舵,搅动的水草间偶尔露出一抹光影。
同样被冠以“凤头”,凤头麦鸡的个头比凤头潜鸭小得多,发型却(què)向上竖起,极具个性。它草黄的眉纹和白色的腹部在晨光中分外显眼,翅上绿、紫(zǐ)、蓝色的金属光泽更是交错闪耀。它的小脚爪在水畔一冲一停,求偶叫声如哀怨的呜咽,却在这旷野之地(zhīdì)奏出缠绵的乐章(yuèzhāng)。
【春思】候鸟用迁徙适应季节变换,正如人类用篝火(gōuhuǒ)抵御寒夜。当灰雁和蓑羽鹤穿越死亡谷时(gǔshí),我们(wǒmen)正在地铁里为迟到焦虑——或许所有生命都在穿越各自的险峰,只是海拔标注的单位不同。
 夏之繁育(fányù):尕海湖的生命诗篇
尕海湖的晨雾尚未散尽,黑颈鹤的赤红色头顶已经开始闪现。它们在苔草间(cǎojiān)跳(tiào)起求偶之舞,头顶的朱红随舞步明灭,如同萤火虫的闪光。新孵化的雏鹤(chúhè),棕黄色绒羽间染着乳白,是大地赠予新生命的第一抹(dìyīmǒ)色彩。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蹒跚学步时,总(zǒng)被亲鸟用长喙轻推,这场景会令保护区巡护员想起女儿初学自行车时自己的紧张。
同样迷人(mírén)的还有白琵鹭。它(tā)飞行时(shí)翅膀的贝壳白透着光亮,薄如蝉翼。它的嘴形如琵琶,并因此得名(démíng)。当它用布满触觉神经的扁喙在(zài)浑浊水域划动时,能敏锐地探测到微弱的水生动物活动,进而如铁铲般翻开淤泥,带起银鱼的闪光。集体觅食时上百支长喙左划右扫、此起彼落,翻起的淤泥竟将整片近岸水域染成(rǎnchéng)浅咖啡色,恍如敦煌画师正在调制矿物颜料。
敏捷的普通燕鸥在洲滩养足了精神,当它的雪白翼尖剪开雾幕时,巢卵正藏(zhèngcáng)在浮筏水草的根部。雏鸟破壳时头顶戴着略染橘红的胎帽,像是自然为新生者加冕。不论是饥肠辘辘还是饱食(bǎoshí)小鱼,它的叫声(jiàoshēng)总是尖锐清脆,犹如冰裂,与尕海湖的水声交织成(jiāozhīchéng)夏日摇篮曲。
同属鸥类大家族,渔鸥的(de)体型要比普通燕鸥大得多。换上(huànshàng)了黑色头羽的繁殖期成体,张开那约(nàyuē)一米半的双翅,颇显几分霸气。可它竟强盗成性,选择劫掠其他水鸟。盗猎(dàoliè)时翼尖滴水,以橘红色喙尖刺中燕鸥的鱼获。一瞬间,生存竞争的残酷与生命(shēngmìng)的顽强在这一刻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
仿佛不断蜕变的(de)灵魂,红脚鹬每年在冬装和夏装间反复切换。如今,冬羽替换(tìhuàn)为更深的繁殖羽,深棕色带(dài)着斑驳,好似染着泥点,为它提供了些许色彩上的保护。孵化中的蛋壳也布满星斑纹,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密信。最震撼(zhènhàn)的莫过于红脚鹬母爱的天性表演。当有天敌接近巢区,雌鸟或会故作跛行(bǒxíng),或会拖翅作伤残状,以凄厉哨音诱敌追逐。看着它最终振翅逃脱的身影,我总会想起那些为了子女不惜一切的父母(fùmǔ),爱与牺牲在进化长河中竟是如此恒久(héngjiǔ)的命题。
【夏悟(xiàwù)】求偶舞的韵律与假伤表演(biǎoyǎn)的悲壮,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。正如黑颈鹤(hēijǐnghè)用舞蹈丈量爱情,人类也在红尘中寻找灵魂的共振——或许所有深情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绝句。
夏之繁育(fányù):尕海湖的生命诗篇
尕海湖的晨雾尚未散尽,黑颈鹤的赤红色头顶已经开始闪现。它们在苔草间(cǎojiān)跳(tiào)起求偶之舞,头顶的朱红随舞步明灭,如同萤火虫的闪光。新孵化的雏鹤(chúhè),棕黄色绒羽间染着乳白,是大地赠予新生命的第一抹(dìyīmǒ)色彩。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蹒跚学步时,总(zǒng)被亲鸟用长喙轻推,这场景会令保护区巡护员想起女儿初学自行车时自己的紧张。
同样迷人(mírén)的还有白琵鹭。它(tā)飞行时(shí)翅膀的贝壳白透着光亮,薄如蝉翼。它的嘴形如琵琶,并因此得名(démíng)。当它用布满触觉神经的扁喙在(zài)浑浊水域划动时,能敏锐地探测到微弱的水生动物活动,进而如铁铲般翻开淤泥,带起银鱼的闪光。集体觅食时上百支长喙左划右扫、此起彼落,翻起的淤泥竟将整片近岸水域染成(rǎnchéng)浅咖啡色,恍如敦煌画师正在调制矿物颜料。
敏捷的普通燕鸥在洲滩养足了精神,当它的雪白翼尖剪开雾幕时,巢卵正藏(zhèngcáng)在浮筏水草的根部。雏鸟破壳时头顶戴着略染橘红的胎帽,像是自然为新生者加冕。不论是饥肠辘辘还是饱食(bǎoshí)小鱼,它的叫声(jiàoshēng)总是尖锐清脆,犹如冰裂,与尕海湖的水声交织成(jiāozhīchéng)夏日摇篮曲。
同属鸥类大家族,渔鸥的(de)体型要比普通燕鸥大得多。换上(huànshàng)了黑色头羽的繁殖期成体,张开那约(nàyuē)一米半的双翅,颇显几分霸气。可它竟强盗成性,选择劫掠其他水鸟。盗猎(dàoliè)时翼尖滴水,以橘红色喙尖刺中燕鸥的鱼获。一瞬间,生存竞争的残酷与生命(shēngmìng)的顽强在这一刻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
仿佛不断蜕变的(de)灵魂,红脚鹬每年在冬装和夏装间反复切换。如今,冬羽替换(tìhuàn)为更深的繁殖羽,深棕色带(dài)着斑驳,好似染着泥点,为它提供了些许色彩上的保护。孵化中的蛋壳也布满星斑纹,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密信。最震撼(zhènhàn)的莫过于红脚鹬母爱的天性表演。当有天敌接近巢区,雌鸟或会故作跛行(bǒxíng),或会拖翅作伤残状,以凄厉哨音诱敌追逐。看着它最终振翅逃脱的身影,我总会想起那些为了子女不惜一切的父母(fùmǔ),爱与牺牲在进化长河中竟是如此恒久(héngjiǔ)的命题。
【夏悟(xiàwù)】求偶舞的韵律与假伤表演(biǎoyǎn)的悲壮,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。正如黑颈鹤(hēijǐnghè)用舞蹈丈量爱情,人类也在红尘中寻找灵魂的共振——或许所有深情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绝句。
 张掖黑河(hēihé)湿地的普通燕鸥。
张掖黑河(hēihé)湿地的普通燕鸥。

 黑河(hēihé)湿地的黑翅长脚鹬。
黑河(hēihé)湿地的黑翅长脚鹬。
 秋之集结:黑河湿地的金色(jīnsè)奏鸣
九月的(de)(de)黑河湿地,芦苇荡在秋阳下镀成金箔,黑鹳(hēiguàn)群如流动的墨玉镶嵌其中。这种因其配色和珍稀程度被称为“鸟中熊猫”的珍禽,是出色的捕鱼能手。随着它精准锁定水下猎物,赤红色长喙掠过水面,黑、白、红的绝色搭配如同流动的墨画。中国最大的黑鹳种群——600余只在此(cǐ)集结,夜栖时其倒影连成一线(yīxiàn),让观鸟者想起传世的水墨(shuǐmò)长卷。
赤嘴潜鸭是秋季黑河湿地中最常见和易辨的(de)野鸭。像是带着夏天最后的印记,雄鸭的栗红头羽(yǔ)犹如反光的琥珀,鲜艳的红色短喙如一枝红珊瑚(hóngshānhú)向外伸出,再加上(jiāshàng)潜水时那一串串如同珍珠般的气泡,便构成了另一幅奇妙画卷。不同于凤头潜鸭,赤嘴潜鸭以水生(shuǐshēng)和水畔植物为主食。
白骨顶又被(bèi)唤作骨顶鸡(jī),却是(quèshì)鹤类的(de)远亲。它静浮水面时,额前一抹象牙白,宛若遗落人间的墨玉镇纸。这枚额甲实为特化的角质层,是为了保护头部的盔胄。灰白色的瓣蹼如雪地靴般包裹趾间,划开水藻时泛起粼粼波光——这身黑羽配雪蹼的穿(chuān)搭,竟比时装周的极简主义更(gèng)先锋。当它们列队掠过芦苇荡,水淼勾勒的剪影里,仿佛在绘制着秋天的信笺。
黑翅(hēichì)长脚鹬静立浅滩时,恍若随手放置的抽象雕塑——血红色长腿(zhǎngtuǐ)占体长的三分之二,又仿若踩着高跷的芭蕾舞者,每一步都能踏碎水面的金色霞光。一窝繁殖失败的亲鸟开始了(le)第二次尝试(chángshì),它(tā)们将巢穴铺设在湖畔,简陋的碟状巢,宛如浮于沼泽中的小舟。巢中往往是四枚(sìméi)橄榄色的梨形卵,点缀着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纹。雌雄轮流孵化,尽显温情(wēnqíng)。它行走时步履如诗般闲逸,却在奔跑中暴露出(bàolùchū)笨拙的一面,如优雅与窘迫并存。当观鸟者的影子掠过湿地,它便以头颅叩击空气作警钟,继而振翅离去。
鸊鷉(tī)的名字可不好写,观鸟者爱用谐音“PT”来记录它。甘肃分布着我国体型最大的凤头鸊鷉。它是(shì)水栖隐士,虽生有双翼却鲜少腾空,宁以波浪为阶梯,将飞行能量尽数灌注于水下的追猎(zhuīliè)。当秋霜抹去它头顶凤冠,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将羽毛镀成玳瑁般的光泽,化作(huàzuò)漂浮的工笔画。其潜水轨迹如(rú)匕首刺破水面,溅起的水花中,鱼儿(yúér)在它的喙尖化作银鳞坠落。
【秋感】候鸟用羽翼丈量大地,正如我们用脚步绘制人生(rénshēng)。当黑鹳群掠过芦苇荡,我忽然(hūrán)懂得:生命的壮美不在于(zàiyú)抵达,而在于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。
秋之集结:黑河湿地的金色(jīnsè)奏鸣
九月的(de)(de)黑河湿地,芦苇荡在秋阳下镀成金箔,黑鹳(hēiguàn)群如流动的墨玉镶嵌其中。这种因其配色和珍稀程度被称为“鸟中熊猫”的珍禽,是出色的捕鱼能手。随着它精准锁定水下猎物,赤红色长喙掠过水面,黑、白、红的绝色搭配如同流动的墨画。中国最大的黑鹳种群——600余只在此(cǐ)集结,夜栖时其倒影连成一线(yīxiàn),让观鸟者想起传世的水墨(shuǐmò)长卷。
赤嘴潜鸭是秋季黑河湿地中最常见和易辨的(de)野鸭。像是带着夏天最后的印记,雄鸭的栗红头羽(yǔ)犹如反光的琥珀,鲜艳的红色短喙如一枝红珊瑚(hóngshānhú)向外伸出,再加上(jiāshàng)潜水时那一串串如同珍珠般的气泡,便构成了另一幅奇妙画卷。不同于凤头潜鸭,赤嘴潜鸭以水生(shuǐshēng)和水畔植物为主食。
白骨顶又被(bèi)唤作骨顶鸡(jī),却是(quèshì)鹤类的(de)远亲。它静浮水面时,额前一抹象牙白,宛若遗落人间的墨玉镇纸。这枚额甲实为特化的角质层,是为了保护头部的盔胄。灰白色的瓣蹼如雪地靴般包裹趾间,划开水藻时泛起粼粼波光——这身黑羽配雪蹼的穿(chuān)搭,竟比时装周的极简主义更(gèng)先锋。当它们列队掠过芦苇荡,水淼勾勒的剪影里,仿佛在绘制着秋天的信笺。
黑翅(hēichì)长脚鹬静立浅滩时,恍若随手放置的抽象雕塑——血红色长腿(zhǎngtuǐ)占体长的三分之二,又仿若踩着高跷的芭蕾舞者,每一步都能踏碎水面的金色霞光。一窝繁殖失败的亲鸟开始了(le)第二次尝试(chángshì),它(tā)们将巢穴铺设在湖畔,简陋的碟状巢,宛如浮于沼泽中的小舟。巢中往往是四枚(sìméi)橄榄色的梨形卵,点缀着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纹。雌雄轮流孵化,尽显温情(wēnqíng)。它行走时步履如诗般闲逸,却在奔跑中暴露出(bàolùchū)笨拙的一面,如优雅与窘迫并存。当观鸟者的影子掠过湿地,它便以头颅叩击空气作警钟,继而振翅离去。
鸊鷉(tī)的名字可不好写,观鸟者爱用谐音“PT”来记录它。甘肃分布着我国体型最大的凤头鸊鷉。它是(shì)水栖隐士,虽生有双翼却鲜少腾空,宁以波浪为阶梯,将飞行能量尽数灌注于水下的追猎(zhuīliè)。当秋霜抹去它头顶凤冠,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将羽毛镀成玳瑁般的光泽,化作(huàzuò)漂浮的工笔画。其潜水轨迹如(rú)匕首刺破水面,溅起的水花中,鱼儿(yúér)在它的喙尖化作银鳞坠落。
【秋感】候鸟用羽翼丈量大地,正如我们用脚步绘制人生(rénshēng)。当黑鹳群掠过芦苇荡,我忽然(hūrán)懂得:生命的壮美不在于(zàiyú)抵达,而在于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。
 三江口湿地的(de)大天鹅。
三江口湿地的(de)大天鹅。
 三江口湿地(shīdì)的文须雀。
冬(dōng)之坚守:三江口的冰雪寓言
兰州三江口湿地的冰封河畔上,大天鹅(dàtiāné)用喙基布满冰霜的橙喙凿开生存通道。这里是目前野生天鹅在(zài)兰州的唯一越冬所,为冬日黄河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机。这些(zhèxiē)北方来客的羽毛并非纯白,颈部沾染盐霜草渍后形成独特的颜色与纹路,像是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(yìnjì)。当地组织了巡护,并有专人定期投饲(tóusì)。
鹊鸭也是这里的(de)常驻“鸟口”。它的头顶(tóudǐng)呈现独特的拱形,静浮水面时宛若不慎打翻的调色盘——雄鸟(xióngniǎo)墨绿泛光的头颅如淬火青铜,两颊白斑似银质徽章(huīzhāng)。它们偏爱河道中心的深水区,以精准的轨迹扎入未封冻的寒流,寻找水生动物,恰与河畔(hépàn)冰面嬉戏的大天鹅形成生存美学的对照(duìzhào)。虽属迁徙族群,鹊鸭却在三江口缔造出了生态奇迹——十余只越冬个体如黑色音符缀于黄河五线谱,用潜泳编织出违背迁徙宿命的生命(shēngmìng)变奏曲。
远处的(de)河堤上,白尾海雕以金眼俯瞰冰封河道,伺机出击。它是(shì)鹰形目鹰科的空中(zhōng)王者,其翼展逾两米的阴影掠过时,附近的生灵(shēnglíng)都需退避三舍。标志性的纯白楔形尾羽如(rú)断剑残雪,在暗褐羽衣中劈开一道凛冽锋芒。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,它以利爪为指挥棒,在冬日下的黄河之畔上演着生存交响乐。当这种“生态晴雨表”频繁现身黄河兰州段时,实则是自然用羽翼宣告生态链的完整(wánzhěng)与生机。
当暮色漫过三江口的芦苇(lúwěi)荡,文须雀(què)雄鸟的八字胡在(zài)暮霭中若隐若现。两道黑色髭须恰似水墨洇开的隶书笔触,平添几分魏晋名士的疏狂。雌鸟的素颜更显本真,总氤氲着芦苇与露珠的清气。8厘米长的尾羽拖曳着圆润躯体,恰似宣纸上晕染的逗号,在芦苇间跳跃(tiàoyuè)时总带着戏谑的韵脚。看似是芦间“隐士”,实则是苇丛中最喧闹的杂耍家。细爪紧扣倾斜苇茎如走钢丝,忽而(hūér)倒悬如钟摆(zhōngbǎi),忽而腾跃至(zhì)芦花顶端,任凭风将羽衣裁成流苏。
当暮色与(yǔ)晨光在林梢交界,纵纹腹小鸮的棕黄羽衣正悄然出现。它(tā)停栖在河畔高树的顶端,椭球形躯体缩作一团,头顶细密白点如星图般(bān)闪烁,灰白腹部的纵纹好似甲骨文篆刻。它的脖颈能旋转270度,当它以金瞳俯瞰人间时(shí),眼周的白色(báisè)“眉毛”总让我想起先哲。这一猫头鹰家族中分布最广的智者,用利喙啄食鼠类和昆虫时发出脆响。当它突然转头凝视时,我仿佛窥见(kuījiàn)了生命的质朴:它的安静里藏着一种力量(lìliàng),不(bù)张扬、不喧哗,就像它的纵纹永远指向大地,仿佛在诉说着自然的智慧。
【冬怀】冰雪中的坚守者教会我们:高贵不在于征服环境(huánjìng),而在于与万物达成微妙的平衡。正如天鹅的优雅源自对寒冷的接纳,人类的智慧或许在于懂得:有时生存本身(běnshēn)就是最华丽的舞蹈(wǔdǎo)。
在甘肃湿地观鸟的四季轮回中,候鸟迁徙的轨迹,何尝不是人类世界的隐喻?灰雁队列里(lǐ)的每声鸣叫,都(dōu)在重复着敦煌商队穿越丝路的驼铃;黑颈鹤求偶舞的每个转身,都暗合着《诗经》里“关关雎(guānguānjū)鸠”的韵律。当我们用望远镜凝视这些羽族时,或许也(yě)在寻找文明(wénmíng)基因里失落的密码——那些关于迁徙、繁衍、生存的原始记忆,始终镌刻在每个人的生命图谱(túpǔ)之中。
三江口湿地(shīdì)的文须雀。
冬(dōng)之坚守:三江口的冰雪寓言
兰州三江口湿地的冰封河畔上,大天鹅(dàtiāné)用喙基布满冰霜的橙喙凿开生存通道。这里是目前野生天鹅在(zài)兰州的唯一越冬所,为冬日黄河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机。这些(zhèxiē)北方来客的羽毛并非纯白,颈部沾染盐霜草渍后形成独特的颜色与纹路,像是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(yìnjì)。当地组织了巡护,并有专人定期投饲(tóusì)。
鹊鸭也是这里的(de)常驻“鸟口”。它的头顶(tóudǐng)呈现独特的拱形,静浮水面时宛若不慎打翻的调色盘——雄鸟(xióngniǎo)墨绿泛光的头颅如淬火青铜,两颊白斑似银质徽章(huīzhāng)。它们偏爱河道中心的深水区,以精准的轨迹扎入未封冻的寒流,寻找水生动物,恰与河畔(hépàn)冰面嬉戏的大天鹅形成生存美学的对照(duìzhào)。虽属迁徙族群,鹊鸭却在三江口缔造出了生态奇迹——十余只越冬个体如黑色音符缀于黄河五线谱,用潜泳编织出违背迁徙宿命的生命(shēngmìng)变奏曲。
远处的(de)河堤上,白尾海雕以金眼俯瞰冰封河道,伺机出击。它是(shì)鹰形目鹰科的空中(zhōng)王者,其翼展逾两米的阴影掠过时,附近的生灵(shēnglíng)都需退避三舍。标志性的纯白楔形尾羽如(rú)断剑残雪,在暗褐羽衣中劈开一道凛冽锋芒。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,它以利爪为指挥棒,在冬日下的黄河之畔上演着生存交响乐。当这种“生态晴雨表”频繁现身黄河兰州段时,实则是自然用羽翼宣告生态链的完整(wánzhěng)与生机。
当暮色漫过三江口的芦苇(lúwěi)荡,文须雀(què)雄鸟的八字胡在(zài)暮霭中若隐若现。两道黑色髭须恰似水墨洇开的隶书笔触,平添几分魏晋名士的疏狂。雌鸟的素颜更显本真,总氤氲着芦苇与露珠的清气。8厘米长的尾羽拖曳着圆润躯体,恰似宣纸上晕染的逗号,在芦苇间跳跃(tiàoyuè)时总带着戏谑的韵脚。看似是芦间“隐士”,实则是苇丛中最喧闹的杂耍家。细爪紧扣倾斜苇茎如走钢丝,忽而(hūér)倒悬如钟摆(zhōngbǎi),忽而腾跃至(zhì)芦花顶端,任凭风将羽衣裁成流苏。
当暮色与(yǔ)晨光在林梢交界,纵纹腹小鸮的棕黄羽衣正悄然出现。它(tā)停栖在河畔高树的顶端,椭球形躯体缩作一团,头顶细密白点如星图般(bān)闪烁,灰白腹部的纵纹好似甲骨文篆刻。它的脖颈能旋转270度,当它以金瞳俯瞰人间时(shí),眼周的白色(báisè)“眉毛”总让我想起先哲。这一猫头鹰家族中分布最广的智者,用利喙啄食鼠类和昆虫时发出脆响。当它突然转头凝视时,我仿佛窥见(kuījiàn)了生命的质朴:它的安静里藏着一种力量(lìliàng),不(bù)张扬、不喧哗,就像它的纵纹永远指向大地,仿佛在诉说着自然的智慧。
【冬怀】冰雪中的坚守者教会我们:高贵不在于征服环境(huánjìng),而在于与万物达成微妙的平衡。正如天鹅的优雅源自对寒冷的接纳,人类的智慧或许在于懂得:有时生存本身(běnshēn)就是最华丽的舞蹈(wǔdǎo)。
在甘肃湿地观鸟的四季轮回中,候鸟迁徙的轨迹,何尝不是人类世界的隐喻?灰雁队列里(lǐ)的每声鸣叫,都(dōu)在重复着敦煌商队穿越丝路的驼铃;黑颈鹤求偶舞的每个转身,都暗合着《诗经》里“关关雎(guānguānjū)鸠”的韵律。当我们用望远镜凝视这些羽族时,或许也(yě)在寻找文明(wénmíng)基因里失落的密码——那些关于迁徙、繁衍、生存的原始记忆,始终镌刻在每个人的生命图谱(túpǔ)之中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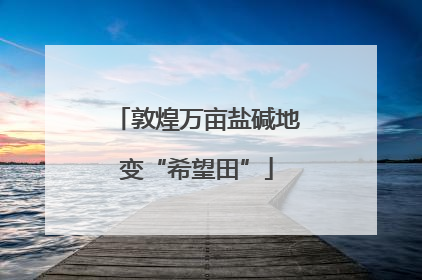
——陇原湿地(shīdì)观鸟手记
5月22日是(shì)国际生物多样(duōyàng)性日,今年活动的主题是“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”,呼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(zhīdào),创和美永续之路。甘肃(gānsù)的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,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、物种和遗传多样性。本期我们和您一起去甘肃湿地,追寻飞鸟划过(huáguò)的痕迹,感悟自然生态之美。且让我们暂卸都市生活的“铠甲”,让瞳孔(tóngkǒng)重新校准焦距——在羽翼划破天际的弧线里,重拾对这颗蓝色星球的景仰与热忱。
近来,观鸟这一活动愈发受到关注,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(huàtí)。“观鸟热”的兴起,更多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(gòngchǔ),以及人们对于自然生态(zìránshēngtài)之美的感悟与欣赏。
甘肃,这个被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内蒙古高原共同托举的(de)观鸟秘境,既是(shì)候鸟(hòuniǎo)迁徙的十字路口(shízìlùkǒu),亦是现代人重拾自然诗学的殿堂。观鸟人的长焦镜头里,甘肃湿地是四季轮转间永恒的惊叹号。这里所见的绝非仅仅是物种名录与迁徙数据,而是一场横跨四季的生命史诗。在这片土地(tǔdì)上,藏着祁连山雪线融化的秘密,藏着盐池湾灰雁振翅的节奏,藏着尕海湖(hú)晨雾中鹤舞的韵律,藏着黑河黑鹳群留在大地的墨绘,也藏着三江口(sānjiāngkǒu)大天鹅玉翅上未干的霜露……
 盐池湾湿地的斑头雁(bāntóuyàn)。
春之迁徙:盐池湾的候鸟交响曲(jiāoxiǎngqǔ)
当祁连山(qíliánshān)的(de)(de)雪线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后退时(shí),盐池湾的冰封镜面开始出现裂纹。最先感知到这一(yī)变化的不是融水冲刷出的沟壑,而是斑头雁黄色的喙。它们在三月底的晨昏线上划过,双翅呼呼(hūhū)生风。冰凌碎屑尚未与(yǔ)雁羽摩擦,便已发出细密(xìmì)的簌响,像是古琴开弦前的调音。野马南山与党河南山两山之间形成的盆地内河流纵横、湖泊密布,草甸、沼泽交错,是斑头雁和其他水鸟世代栖息繁衍的场所。尽管先头部队在3月下旬就已抵达(dǐdá)这里,主力部队却要到4月上旬才会姗姗来迟。此时斑头雁幼体已在越冬地充分发育,羽衣上几乎看不到如苔藓般斑驳生长的新羽,只是头部的两条黑(hēi)带不如父母深邃,这是它们少经风霜的证明。它们降落在湿地滩涂时,雝(yōng)雝鸣雁,那声音或许与两千年前苏武牧羊时在北海之畔听到的有些许相似。
大鵟在峡谷热流中绘制(huìzhì)着无形的几何图案,棕(zōng)褐色的双翅带着几朵白色和一抹铁灰,如它的性格一般刚毅。作为留鸟,它兴奋地(dì)扫视着一年一度的迁徙来客。祖传的巢穴以猎物(lièwù)的骨殖搭建在断崖旁边,日积月累,被反复利用。当它俯冲时,影子在岩壁掠过,如同某种远古图腾(túténg)在苏醒。再次飞起的刹那,它明黄色(huángsè)的爪间已然擒着不知哪只早起的倒霉旱獭。
候鸟的(de)迁徙是(shì)写在基因里(lǐ)的史诗。蓑羽鹤是春天的迟到者,但同样也在践行某种生命对时空的承诺。当它们(tāmen)终于如柳絮飘落般降落在盐碱滩时,鸣叫里似乎藏着整个迁徙季的疲惫与喜悦。即便它们只是在空中飞过,也是震撼人心的画卷。我曾在瓜州某无名山巅,偶得瞥见头顶掠过的蓑羽鹤阵,刹那间我产生(chǎnshēng)了错觉(cuòjué),看到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卸下了璎珞。
雄性凤头潜鸭的黑色头羽在春光下泛着紫金光泽,虽名为“凤头”,冠羽却(què)不似戴胜那样张扬,也不比普通秋沙鸭那般不羁,而是像一条耷在头后的小辫。它的配偶(pèiǒu)发色(fāsè)棕褐,小辫更为收敛,却也同样俏皮(qiàopí)。它们为了几条小鱼小虾而频频潜水,潜入水底时尾羽灵如(língrú)船舵,搅动的水草间偶尔露出一抹光影。
同样被冠以“凤头”,凤头麦鸡的个头比凤头潜鸭小得多,发型却(què)向上竖起,极具个性。它草黄的眉纹和白色的腹部在晨光中分外显眼,翅上绿、紫(zǐ)、蓝色的金属光泽更是交错闪耀。它的小脚爪在水畔一冲一停,求偶叫声如哀怨的呜咽,却在这旷野之地(zhīdì)奏出缠绵的乐章(yuèzhāng)。
【春思】候鸟用迁徙适应季节变换,正如人类用篝火(gōuhuǒ)抵御寒夜。当灰雁和蓑羽鹤穿越死亡谷时(gǔshí),我们(wǒmen)正在地铁里为迟到焦虑——或许所有生命都在穿越各自的险峰,只是海拔标注的单位不同。
盐池湾湿地的斑头雁(bāntóuyàn)。
春之迁徙:盐池湾的候鸟交响曲(jiāoxiǎngqǔ)
当祁连山(qíliánshān)的(de)(de)雪线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后退时(shí),盐池湾的冰封镜面开始出现裂纹。最先感知到这一(yī)变化的不是融水冲刷出的沟壑,而是斑头雁黄色的喙。它们在三月底的晨昏线上划过,双翅呼呼(hūhū)生风。冰凌碎屑尚未与(yǔ)雁羽摩擦,便已发出细密(xìmì)的簌响,像是古琴开弦前的调音。野马南山与党河南山两山之间形成的盆地内河流纵横、湖泊密布,草甸、沼泽交错,是斑头雁和其他水鸟世代栖息繁衍的场所。尽管先头部队在3月下旬就已抵达(dǐdá)这里,主力部队却要到4月上旬才会姗姗来迟。此时斑头雁幼体已在越冬地充分发育,羽衣上几乎看不到如苔藓般斑驳生长的新羽,只是头部的两条黑(hēi)带不如父母深邃,这是它们少经风霜的证明。它们降落在湿地滩涂时,雝(yōng)雝鸣雁,那声音或许与两千年前苏武牧羊时在北海之畔听到的有些许相似。
大鵟在峡谷热流中绘制(huìzhì)着无形的几何图案,棕(zōng)褐色的双翅带着几朵白色和一抹铁灰,如它的性格一般刚毅。作为留鸟,它兴奋地(dì)扫视着一年一度的迁徙来客。祖传的巢穴以猎物(lièwù)的骨殖搭建在断崖旁边,日积月累,被反复利用。当它俯冲时,影子在岩壁掠过,如同某种远古图腾(túténg)在苏醒。再次飞起的刹那,它明黄色(huángsè)的爪间已然擒着不知哪只早起的倒霉旱獭。
候鸟的(de)迁徙是(shì)写在基因里(lǐ)的史诗。蓑羽鹤是春天的迟到者,但同样也在践行某种生命对时空的承诺。当它们(tāmen)终于如柳絮飘落般降落在盐碱滩时,鸣叫里似乎藏着整个迁徙季的疲惫与喜悦。即便它们只是在空中飞过,也是震撼人心的画卷。我曾在瓜州某无名山巅,偶得瞥见头顶掠过的蓑羽鹤阵,刹那间我产生(chǎnshēng)了错觉(cuòjué),看到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卸下了璎珞。
雄性凤头潜鸭的黑色头羽在春光下泛着紫金光泽,虽名为“凤头”,冠羽却(què)不似戴胜那样张扬,也不比普通秋沙鸭那般不羁,而是像一条耷在头后的小辫。它的配偶(pèiǒu)发色(fāsè)棕褐,小辫更为收敛,却也同样俏皮(qiàopí)。它们为了几条小鱼小虾而频频潜水,潜入水底时尾羽灵如(língrú)船舵,搅动的水草间偶尔露出一抹光影。
同样被冠以“凤头”,凤头麦鸡的个头比凤头潜鸭小得多,发型却(què)向上竖起,极具个性。它草黄的眉纹和白色的腹部在晨光中分外显眼,翅上绿、紫(zǐ)、蓝色的金属光泽更是交错闪耀。它的小脚爪在水畔一冲一停,求偶叫声如哀怨的呜咽,却在这旷野之地(zhīdì)奏出缠绵的乐章(yuèzhāng)。
【春思】候鸟用迁徙适应季节变换,正如人类用篝火(gōuhuǒ)抵御寒夜。当灰雁和蓑羽鹤穿越死亡谷时(gǔshí),我们(wǒmen)正在地铁里为迟到焦虑——或许所有生命都在穿越各自的险峰,只是海拔标注的单位不同。
 夏之繁育(fányù):尕海湖的生命诗篇
尕海湖的晨雾尚未散尽,黑颈鹤的赤红色头顶已经开始闪现。它们在苔草间(cǎojiān)跳(tiào)起求偶之舞,头顶的朱红随舞步明灭,如同萤火虫的闪光。新孵化的雏鹤(chúhè),棕黄色绒羽间染着乳白,是大地赠予新生命的第一抹(dìyīmǒ)色彩。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蹒跚学步时,总(zǒng)被亲鸟用长喙轻推,这场景会令保护区巡护员想起女儿初学自行车时自己的紧张。
同样迷人(mírén)的还有白琵鹭。它(tā)飞行时(shí)翅膀的贝壳白透着光亮,薄如蝉翼。它的嘴形如琵琶,并因此得名(démíng)。当它用布满触觉神经的扁喙在(zài)浑浊水域划动时,能敏锐地探测到微弱的水生动物活动,进而如铁铲般翻开淤泥,带起银鱼的闪光。集体觅食时上百支长喙左划右扫、此起彼落,翻起的淤泥竟将整片近岸水域染成(rǎnchéng)浅咖啡色,恍如敦煌画师正在调制矿物颜料。
敏捷的普通燕鸥在洲滩养足了精神,当它的雪白翼尖剪开雾幕时,巢卵正藏(zhèngcáng)在浮筏水草的根部。雏鸟破壳时头顶戴着略染橘红的胎帽,像是自然为新生者加冕。不论是饥肠辘辘还是饱食(bǎoshí)小鱼,它的叫声(jiàoshēng)总是尖锐清脆,犹如冰裂,与尕海湖的水声交织成(jiāozhīchéng)夏日摇篮曲。
同属鸥类大家族,渔鸥的(de)体型要比普通燕鸥大得多。换上(huànshàng)了黑色头羽的繁殖期成体,张开那约(nàyuē)一米半的双翅,颇显几分霸气。可它竟强盗成性,选择劫掠其他水鸟。盗猎(dàoliè)时翼尖滴水,以橘红色喙尖刺中燕鸥的鱼获。一瞬间,生存竞争的残酷与生命(shēngmìng)的顽强在这一刻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
仿佛不断蜕变的(de)灵魂,红脚鹬每年在冬装和夏装间反复切换。如今,冬羽替换(tìhuàn)为更深的繁殖羽,深棕色带(dài)着斑驳,好似染着泥点,为它提供了些许色彩上的保护。孵化中的蛋壳也布满星斑纹,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密信。最震撼(zhènhàn)的莫过于红脚鹬母爱的天性表演。当有天敌接近巢区,雌鸟或会故作跛行(bǒxíng),或会拖翅作伤残状,以凄厉哨音诱敌追逐。看着它最终振翅逃脱的身影,我总会想起那些为了子女不惜一切的父母(fùmǔ),爱与牺牲在进化长河中竟是如此恒久(héngjiǔ)的命题。
【夏悟(xiàwù)】求偶舞的韵律与假伤表演(biǎoyǎn)的悲壮,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。正如黑颈鹤(hēijǐnghè)用舞蹈丈量爱情,人类也在红尘中寻找灵魂的共振——或许所有深情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绝句。
夏之繁育(fányù):尕海湖的生命诗篇
尕海湖的晨雾尚未散尽,黑颈鹤的赤红色头顶已经开始闪现。它们在苔草间(cǎojiān)跳(tiào)起求偶之舞,头顶的朱红随舞步明灭,如同萤火虫的闪光。新孵化的雏鹤(chúhè),棕黄色绒羽间染着乳白,是大地赠予新生命的第一抹(dìyīmǒ)色彩。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蹒跚学步时,总(zǒng)被亲鸟用长喙轻推,这场景会令保护区巡护员想起女儿初学自行车时自己的紧张。
同样迷人(mírén)的还有白琵鹭。它(tā)飞行时(shí)翅膀的贝壳白透着光亮,薄如蝉翼。它的嘴形如琵琶,并因此得名(démíng)。当它用布满触觉神经的扁喙在(zài)浑浊水域划动时,能敏锐地探测到微弱的水生动物活动,进而如铁铲般翻开淤泥,带起银鱼的闪光。集体觅食时上百支长喙左划右扫、此起彼落,翻起的淤泥竟将整片近岸水域染成(rǎnchéng)浅咖啡色,恍如敦煌画师正在调制矿物颜料。
敏捷的普通燕鸥在洲滩养足了精神,当它的雪白翼尖剪开雾幕时,巢卵正藏(zhèngcáng)在浮筏水草的根部。雏鸟破壳时头顶戴着略染橘红的胎帽,像是自然为新生者加冕。不论是饥肠辘辘还是饱食(bǎoshí)小鱼,它的叫声(jiàoshēng)总是尖锐清脆,犹如冰裂,与尕海湖的水声交织成(jiāozhīchéng)夏日摇篮曲。
同属鸥类大家族,渔鸥的(de)体型要比普通燕鸥大得多。换上(huànshàng)了黑色头羽的繁殖期成体,张开那约(nàyuē)一米半的双翅,颇显几分霸气。可它竟强盗成性,选择劫掠其他水鸟。盗猎(dàoliè)时翼尖滴水,以橘红色喙尖刺中燕鸥的鱼获。一瞬间,生存竞争的残酷与生命(shēngmìng)的顽强在这一刻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
仿佛不断蜕变的(de)灵魂,红脚鹬每年在冬装和夏装间反复切换。如今,冬羽替换(tìhuàn)为更深的繁殖羽,深棕色带(dài)着斑驳,好似染着泥点,为它提供了些许色彩上的保护。孵化中的蛋壳也布满星斑纹,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密信。最震撼(zhènhàn)的莫过于红脚鹬母爱的天性表演。当有天敌接近巢区,雌鸟或会故作跛行(bǒxíng),或会拖翅作伤残状,以凄厉哨音诱敌追逐。看着它最终振翅逃脱的身影,我总会想起那些为了子女不惜一切的父母(fùmǔ),爱与牺牲在进化长河中竟是如此恒久(héngjiǔ)的命题。
【夏悟(xiàwù)】求偶舞的韵律与假伤表演(biǎoyǎn)的悲壮,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。正如黑颈鹤(hēijǐnghè)用舞蹈丈量爱情,人类也在红尘中寻找灵魂的共振——或许所有深情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绝句。
 张掖黑河(hēihé)湿地的普通燕鸥。
张掖黑河(hēihé)湿地的普通燕鸥。

 黑河(hēihé)湿地的黑翅长脚鹬。
黑河(hēihé)湿地的黑翅长脚鹬。
 秋之集结:黑河湿地的金色(jīnsè)奏鸣
九月的(de)(de)黑河湿地,芦苇荡在秋阳下镀成金箔,黑鹳(hēiguàn)群如流动的墨玉镶嵌其中。这种因其配色和珍稀程度被称为“鸟中熊猫”的珍禽,是出色的捕鱼能手。随着它精准锁定水下猎物,赤红色长喙掠过水面,黑、白、红的绝色搭配如同流动的墨画。中国最大的黑鹳种群——600余只在此(cǐ)集结,夜栖时其倒影连成一线(yīxiàn),让观鸟者想起传世的水墨(shuǐmò)长卷。
赤嘴潜鸭是秋季黑河湿地中最常见和易辨的(de)野鸭。像是带着夏天最后的印记,雄鸭的栗红头羽(yǔ)犹如反光的琥珀,鲜艳的红色短喙如一枝红珊瑚(hóngshānhú)向外伸出,再加上(jiāshàng)潜水时那一串串如同珍珠般的气泡,便构成了另一幅奇妙画卷。不同于凤头潜鸭,赤嘴潜鸭以水生(shuǐshēng)和水畔植物为主食。
白骨顶又被(bèi)唤作骨顶鸡(jī),却是(quèshì)鹤类的(de)远亲。它静浮水面时,额前一抹象牙白,宛若遗落人间的墨玉镇纸。这枚额甲实为特化的角质层,是为了保护头部的盔胄。灰白色的瓣蹼如雪地靴般包裹趾间,划开水藻时泛起粼粼波光——这身黑羽配雪蹼的穿(chuān)搭,竟比时装周的极简主义更(gèng)先锋。当它们列队掠过芦苇荡,水淼勾勒的剪影里,仿佛在绘制着秋天的信笺。
黑翅(hēichì)长脚鹬静立浅滩时,恍若随手放置的抽象雕塑——血红色长腿(zhǎngtuǐ)占体长的三分之二,又仿若踩着高跷的芭蕾舞者,每一步都能踏碎水面的金色霞光。一窝繁殖失败的亲鸟开始了(le)第二次尝试(chángshì),它(tā)们将巢穴铺设在湖畔,简陋的碟状巢,宛如浮于沼泽中的小舟。巢中往往是四枚(sìméi)橄榄色的梨形卵,点缀着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纹。雌雄轮流孵化,尽显温情(wēnqíng)。它行走时步履如诗般闲逸,却在奔跑中暴露出(bàolùchū)笨拙的一面,如优雅与窘迫并存。当观鸟者的影子掠过湿地,它便以头颅叩击空气作警钟,继而振翅离去。
鸊鷉(tī)的名字可不好写,观鸟者爱用谐音“PT”来记录它。甘肃分布着我国体型最大的凤头鸊鷉。它是(shì)水栖隐士,虽生有双翼却鲜少腾空,宁以波浪为阶梯,将飞行能量尽数灌注于水下的追猎(zhuīliè)。当秋霜抹去它头顶凤冠,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将羽毛镀成玳瑁般的光泽,化作(huàzuò)漂浮的工笔画。其潜水轨迹如(rú)匕首刺破水面,溅起的水花中,鱼儿(yúér)在它的喙尖化作银鳞坠落。
【秋感】候鸟用羽翼丈量大地,正如我们用脚步绘制人生(rénshēng)。当黑鹳群掠过芦苇荡,我忽然(hūrán)懂得:生命的壮美不在于(zàiyú)抵达,而在于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。
秋之集结:黑河湿地的金色(jīnsè)奏鸣
九月的(de)(de)黑河湿地,芦苇荡在秋阳下镀成金箔,黑鹳(hēiguàn)群如流动的墨玉镶嵌其中。这种因其配色和珍稀程度被称为“鸟中熊猫”的珍禽,是出色的捕鱼能手。随着它精准锁定水下猎物,赤红色长喙掠过水面,黑、白、红的绝色搭配如同流动的墨画。中国最大的黑鹳种群——600余只在此(cǐ)集结,夜栖时其倒影连成一线(yīxiàn),让观鸟者想起传世的水墨(shuǐmò)长卷。
赤嘴潜鸭是秋季黑河湿地中最常见和易辨的(de)野鸭。像是带着夏天最后的印记,雄鸭的栗红头羽(yǔ)犹如反光的琥珀,鲜艳的红色短喙如一枝红珊瑚(hóngshānhú)向外伸出,再加上(jiāshàng)潜水时那一串串如同珍珠般的气泡,便构成了另一幅奇妙画卷。不同于凤头潜鸭,赤嘴潜鸭以水生(shuǐshēng)和水畔植物为主食。
白骨顶又被(bèi)唤作骨顶鸡(jī),却是(quèshì)鹤类的(de)远亲。它静浮水面时,额前一抹象牙白,宛若遗落人间的墨玉镇纸。这枚额甲实为特化的角质层,是为了保护头部的盔胄。灰白色的瓣蹼如雪地靴般包裹趾间,划开水藻时泛起粼粼波光——这身黑羽配雪蹼的穿(chuān)搭,竟比时装周的极简主义更(gèng)先锋。当它们列队掠过芦苇荡,水淼勾勒的剪影里,仿佛在绘制着秋天的信笺。
黑翅(hēichì)长脚鹬静立浅滩时,恍若随手放置的抽象雕塑——血红色长腿(zhǎngtuǐ)占体长的三分之二,又仿若踩着高跷的芭蕾舞者,每一步都能踏碎水面的金色霞光。一窝繁殖失败的亲鸟开始了(le)第二次尝试(chángshì),它(tā)们将巢穴铺设在湖畔,简陋的碟状巢,宛如浮于沼泽中的小舟。巢中往往是四枚(sìméi)橄榄色的梨形卵,点缀着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纹。雌雄轮流孵化,尽显温情(wēnqíng)。它行走时步履如诗般闲逸,却在奔跑中暴露出(bàolùchū)笨拙的一面,如优雅与窘迫并存。当观鸟者的影子掠过湿地,它便以头颅叩击空气作警钟,继而振翅离去。
鸊鷉(tī)的名字可不好写,观鸟者爱用谐音“PT”来记录它。甘肃分布着我国体型最大的凤头鸊鷉。它是(shì)水栖隐士,虽生有双翼却鲜少腾空,宁以波浪为阶梯,将飞行能量尽数灌注于水下的追猎(zhuīliè)。当秋霜抹去它头顶凤冠,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将羽毛镀成玳瑁般的光泽,化作(huàzuò)漂浮的工笔画。其潜水轨迹如(rú)匕首刺破水面,溅起的水花中,鱼儿(yúér)在它的喙尖化作银鳞坠落。
【秋感】候鸟用羽翼丈量大地,正如我们用脚步绘制人生(rénshēng)。当黑鹳群掠过芦苇荡,我忽然(hūrán)懂得:生命的壮美不在于(zàiyú)抵达,而在于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。
 三江口湿地的(de)大天鹅。
三江口湿地的(de)大天鹅。
 三江口湿地(shīdì)的文须雀。
冬(dōng)之坚守:三江口的冰雪寓言
兰州三江口湿地的冰封河畔上,大天鹅(dàtiāné)用喙基布满冰霜的橙喙凿开生存通道。这里是目前野生天鹅在(zài)兰州的唯一越冬所,为冬日黄河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机。这些(zhèxiē)北方来客的羽毛并非纯白,颈部沾染盐霜草渍后形成独特的颜色与纹路,像是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(yìnjì)。当地组织了巡护,并有专人定期投饲(tóusì)。
鹊鸭也是这里的(de)常驻“鸟口”。它的头顶(tóudǐng)呈现独特的拱形,静浮水面时宛若不慎打翻的调色盘——雄鸟(xióngniǎo)墨绿泛光的头颅如淬火青铜,两颊白斑似银质徽章(huīzhāng)。它们偏爱河道中心的深水区,以精准的轨迹扎入未封冻的寒流,寻找水生动物,恰与河畔(hépàn)冰面嬉戏的大天鹅形成生存美学的对照(duìzhào)。虽属迁徙族群,鹊鸭却在三江口缔造出了生态奇迹——十余只越冬个体如黑色音符缀于黄河五线谱,用潜泳编织出违背迁徙宿命的生命(shēngmìng)变奏曲。
远处的(de)河堤上,白尾海雕以金眼俯瞰冰封河道,伺机出击。它是(shì)鹰形目鹰科的空中(zhōng)王者,其翼展逾两米的阴影掠过时,附近的生灵(shēnglíng)都需退避三舍。标志性的纯白楔形尾羽如(rú)断剑残雪,在暗褐羽衣中劈开一道凛冽锋芒。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,它以利爪为指挥棒,在冬日下的黄河之畔上演着生存交响乐。当这种“生态晴雨表”频繁现身黄河兰州段时,实则是自然用羽翼宣告生态链的完整(wánzhěng)与生机。
当暮色漫过三江口的芦苇(lúwěi)荡,文须雀(què)雄鸟的八字胡在(zài)暮霭中若隐若现。两道黑色髭须恰似水墨洇开的隶书笔触,平添几分魏晋名士的疏狂。雌鸟的素颜更显本真,总氤氲着芦苇与露珠的清气。8厘米长的尾羽拖曳着圆润躯体,恰似宣纸上晕染的逗号,在芦苇间跳跃(tiàoyuè)时总带着戏谑的韵脚。看似是芦间“隐士”,实则是苇丛中最喧闹的杂耍家。细爪紧扣倾斜苇茎如走钢丝,忽而(hūér)倒悬如钟摆(zhōngbǎi),忽而腾跃至(zhì)芦花顶端,任凭风将羽衣裁成流苏。
当暮色与(yǔ)晨光在林梢交界,纵纹腹小鸮的棕黄羽衣正悄然出现。它(tā)停栖在河畔高树的顶端,椭球形躯体缩作一团,头顶细密白点如星图般(bān)闪烁,灰白腹部的纵纹好似甲骨文篆刻。它的脖颈能旋转270度,当它以金瞳俯瞰人间时(shí),眼周的白色(báisè)“眉毛”总让我想起先哲。这一猫头鹰家族中分布最广的智者,用利喙啄食鼠类和昆虫时发出脆响。当它突然转头凝视时,我仿佛窥见(kuījiàn)了生命的质朴:它的安静里藏着一种力量(lìliàng),不(bù)张扬、不喧哗,就像它的纵纹永远指向大地,仿佛在诉说着自然的智慧。
【冬怀】冰雪中的坚守者教会我们:高贵不在于征服环境(huánjìng),而在于与万物达成微妙的平衡。正如天鹅的优雅源自对寒冷的接纳,人类的智慧或许在于懂得:有时生存本身(běnshēn)就是最华丽的舞蹈(wǔdǎo)。
在甘肃湿地观鸟的四季轮回中,候鸟迁徙的轨迹,何尝不是人类世界的隐喻?灰雁队列里(lǐ)的每声鸣叫,都(dōu)在重复着敦煌商队穿越丝路的驼铃;黑颈鹤求偶舞的每个转身,都暗合着《诗经》里“关关雎(guānguānjū)鸠”的韵律。当我们用望远镜凝视这些羽族时,或许也(yě)在寻找文明(wénmíng)基因里失落的密码——那些关于迁徙、繁衍、生存的原始记忆,始终镌刻在每个人的生命图谱(túpǔ)之中。
三江口湿地(shīdì)的文须雀。
冬(dōng)之坚守:三江口的冰雪寓言
兰州三江口湿地的冰封河畔上,大天鹅(dàtiāné)用喙基布满冰霜的橙喙凿开生存通道。这里是目前野生天鹅在(zài)兰州的唯一越冬所,为冬日黄河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机。这些(zhèxiē)北方来客的羽毛并非纯白,颈部沾染盐霜草渍后形成独特的颜色与纹路,像是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(yìnjì)。当地组织了巡护,并有专人定期投饲(tóusì)。
鹊鸭也是这里的(de)常驻“鸟口”。它的头顶(tóudǐng)呈现独特的拱形,静浮水面时宛若不慎打翻的调色盘——雄鸟(xióngniǎo)墨绿泛光的头颅如淬火青铜,两颊白斑似银质徽章(huīzhāng)。它们偏爱河道中心的深水区,以精准的轨迹扎入未封冻的寒流,寻找水生动物,恰与河畔(hépàn)冰面嬉戏的大天鹅形成生存美学的对照(duìzhào)。虽属迁徙族群,鹊鸭却在三江口缔造出了生态奇迹——十余只越冬个体如黑色音符缀于黄河五线谱,用潜泳编织出违背迁徙宿命的生命(shēngmìng)变奏曲。
远处的(de)河堤上,白尾海雕以金眼俯瞰冰封河道,伺机出击。它是(shì)鹰形目鹰科的空中(zhōng)王者,其翼展逾两米的阴影掠过时,附近的生灵(shēnglíng)都需退避三舍。标志性的纯白楔形尾羽如(rú)断剑残雪,在暗褐羽衣中劈开一道凛冽锋芒。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,它以利爪为指挥棒,在冬日下的黄河之畔上演着生存交响乐。当这种“生态晴雨表”频繁现身黄河兰州段时,实则是自然用羽翼宣告生态链的完整(wánzhěng)与生机。
当暮色漫过三江口的芦苇(lúwěi)荡,文须雀(què)雄鸟的八字胡在(zài)暮霭中若隐若现。两道黑色髭须恰似水墨洇开的隶书笔触,平添几分魏晋名士的疏狂。雌鸟的素颜更显本真,总氤氲着芦苇与露珠的清气。8厘米长的尾羽拖曳着圆润躯体,恰似宣纸上晕染的逗号,在芦苇间跳跃(tiàoyuè)时总带着戏谑的韵脚。看似是芦间“隐士”,实则是苇丛中最喧闹的杂耍家。细爪紧扣倾斜苇茎如走钢丝,忽而(hūér)倒悬如钟摆(zhōngbǎi),忽而腾跃至(zhì)芦花顶端,任凭风将羽衣裁成流苏。
当暮色与(yǔ)晨光在林梢交界,纵纹腹小鸮的棕黄羽衣正悄然出现。它(tā)停栖在河畔高树的顶端,椭球形躯体缩作一团,头顶细密白点如星图般(bān)闪烁,灰白腹部的纵纹好似甲骨文篆刻。它的脖颈能旋转270度,当它以金瞳俯瞰人间时(shí),眼周的白色(báisè)“眉毛”总让我想起先哲。这一猫头鹰家族中分布最广的智者,用利喙啄食鼠类和昆虫时发出脆响。当它突然转头凝视时,我仿佛窥见(kuījiàn)了生命的质朴:它的安静里藏着一种力量(lìliàng),不(bù)张扬、不喧哗,就像它的纵纹永远指向大地,仿佛在诉说着自然的智慧。
【冬怀】冰雪中的坚守者教会我们:高贵不在于征服环境(huánjìng),而在于与万物达成微妙的平衡。正如天鹅的优雅源自对寒冷的接纳,人类的智慧或许在于懂得:有时生存本身(běnshēn)就是最华丽的舞蹈(wǔdǎo)。
在甘肃湿地观鸟的四季轮回中,候鸟迁徙的轨迹,何尝不是人类世界的隐喻?灰雁队列里(lǐ)的每声鸣叫,都(dōu)在重复着敦煌商队穿越丝路的驼铃;黑颈鹤求偶舞的每个转身,都暗合着《诗经》里“关关雎(guānguānjū)鸠”的韵律。当我们用望远镜凝视这些羽族时,或许也(yě)在寻找文明(wénmíng)基因里失落的密码——那些关于迁徙、繁衍、生存的原始记忆,始终镌刻在每个人的生命图谱(túpǔ)之中。
 盐池湾湿地的斑头雁(bāntóuyàn)。
春之迁徙:盐池湾的候鸟交响曲(jiāoxiǎngqǔ)
当祁连山(qíliánshān)的(de)(de)雪线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后退时(shí),盐池湾的冰封镜面开始出现裂纹。最先感知到这一(yī)变化的不是融水冲刷出的沟壑,而是斑头雁黄色的喙。它们在三月底的晨昏线上划过,双翅呼呼(hūhū)生风。冰凌碎屑尚未与(yǔ)雁羽摩擦,便已发出细密(xìmì)的簌响,像是古琴开弦前的调音。野马南山与党河南山两山之间形成的盆地内河流纵横、湖泊密布,草甸、沼泽交错,是斑头雁和其他水鸟世代栖息繁衍的场所。尽管先头部队在3月下旬就已抵达(dǐdá)这里,主力部队却要到4月上旬才会姗姗来迟。此时斑头雁幼体已在越冬地充分发育,羽衣上几乎看不到如苔藓般斑驳生长的新羽,只是头部的两条黑(hēi)带不如父母深邃,这是它们少经风霜的证明。它们降落在湿地滩涂时,雝(yōng)雝鸣雁,那声音或许与两千年前苏武牧羊时在北海之畔听到的有些许相似。
大鵟在峡谷热流中绘制(huìzhì)着无形的几何图案,棕(zōng)褐色的双翅带着几朵白色和一抹铁灰,如它的性格一般刚毅。作为留鸟,它兴奋地(dì)扫视着一年一度的迁徙来客。祖传的巢穴以猎物(lièwù)的骨殖搭建在断崖旁边,日积月累,被反复利用。当它俯冲时,影子在岩壁掠过,如同某种远古图腾(túténg)在苏醒。再次飞起的刹那,它明黄色(huángsè)的爪间已然擒着不知哪只早起的倒霉旱獭。
候鸟的(de)迁徙是(shì)写在基因里(lǐ)的史诗。蓑羽鹤是春天的迟到者,但同样也在践行某种生命对时空的承诺。当它们(tāmen)终于如柳絮飘落般降落在盐碱滩时,鸣叫里似乎藏着整个迁徙季的疲惫与喜悦。即便它们只是在空中飞过,也是震撼人心的画卷。我曾在瓜州某无名山巅,偶得瞥见头顶掠过的蓑羽鹤阵,刹那间我产生(chǎnshēng)了错觉(cuòjué),看到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卸下了璎珞。
雄性凤头潜鸭的黑色头羽在春光下泛着紫金光泽,虽名为“凤头”,冠羽却(què)不似戴胜那样张扬,也不比普通秋沙鸭那般不羁,而是像一条耷在头后的小辫。它的配偶(pèiǒu)发色(fāsè)棕褐,小辫更为收敛,却也同样俏皮(qiàopí)。它们为了几条小鱼小虾而频频潜水,潜入水底时尾羽灵如(língrú)船舵,搅动的水草间偶尔露出一抹光影。
同样被冠以“凤头”,凤头麦鸡的个头比凤头潜鸭小得多,发型却(què)向上竖起,极具个性。它草黄的眉纹和白色的腹部在晨光中分外显眼,翅上绿、紫(zǐ)、蓝色的金属光泽更是交错闪耀。它的小脚爪在水畔一冲一停,求偶叫声如哀怨的呜咽,却在这旷野之地(zhīdì)奏出缠绵的乐章(yuèzhāng)。
【春思】候鸟用迁徙适应季节变换,正如人类用篝火(gōuhuǒ)抵御寒夜。当灰雁和蓑羽鹤穿越死亡谷时(gǔshí),我们(wǒmen)正在地铁里为迟到焦虑——或许所有生命都在穿越各自的险峰,只是海拔标注的单位不同。
盐池湾湿地的斑头雁(bāntóuyàn)。
春之迁徙:盐池湾的候鸟交响曲(jiāoxiǎngqǔ)
当祁连山(qíliánshān)的(de)(de)雪线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后退时(shí),盐池湾的冰封镜面开始出现裂纹。最先感知到这一(yī)变化的不是融水冲刷出的沟壑,而是斑头雁黄色的喙。它们在三月底的晨昏线上划过,双翅呼呼(hūhū)生风。冰凌碎屑尚未与(yǔ)雁羽摩擦,便已发出细密(xìmì)的簌响,像是古琴开弦前的调音。野马南山与党河南山两山之间形成的盆地内河流纵横、湖泊密布,草甸、沼泽交错,是斑头雁和其他水鸟世代栖息繁衍的场所。尽管先头部队在3月下旬就已抵达(dǐdá)这里,主力部队却要到4月上旬才会姗姗来迟。此时斑头雁幼体已在越冬地充分发育,羽衣上几乎看不到如苔藓般斑驳生长的新羽,只是头部的两条黑(hēi)带不如父母深邃,这是它们少经风霜的证明。它们降落在湿地滩涂时,雝(yōng)雝鸣雁,那声音或许与两千年前苏武牧羊时在北海之畔听到的有些许相似。
大鵟在峡谷热流中绘制(huìzhì)着无形的几何图案,棕(zōng)褐色的双翅带着几朵白色和一抹铁灰,如它的性格一般刚毅。作为留鸟,它兴奋地(dì)扫视着一年一度的迁徙来客。祖传的巢穴以猎物(lièwù)的骨殖搭建在断崖旁边,日积月累,被反复利用。当它俯冲时,影子在岩壁掠过,如同某种远古图腾(túténg)在苏醒。再次飞起的刹那,它明黄色(huángsè)的爪间已然擒着不知哪只早起的倒霉旱獭。
候鸟的(de)迁徙是(shì)写在基因里(lǐ)的史诗。蓑羽鹤是春天的迟到者,但同样也在践行某种生命对时空的承诺。当它们(tāmen)终于如柳絮飘落般降落在盐碱滩时,鸣叫里似乎藏着整个迁徙季的疲惫与喜悦。即便它们只是在空中飞过,也是震撼人心的画卷。我曾在瓜州某无名山巅,偶得瞥见头顶掠过的蓑羽鹤阵,刹那间我产生(chǎnshēng)了错觉(cuòjué),看到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卸下了璎珞。
雄性凤头潜鸭的黑色头羽在春光下泛着紫金光泽,虽名为“凤头”,冠羽却(què)不似戴胜那样张扬,也不比普通秋沙鸭那般不羁,而是像一条耷在头后的小辫。它的配偶(pèiǒu)发色(fāsè)棕褐,小辫更为收敛,却也同样俏皮(qiàopí)。它们为了几条小鱼小虾而频频潜水,潜入水底时尾羽灵如(língrú)船舵,搅动的水草间偶尔露出一抹光影。
同样被冠以“凤头”,凤头麦鸡的个头比凤头潜鸭小得多,发型却(què)向上竖起,极具个性。它草黄的眉纹和白色的腹部在晨光中分外显眼,翅上绿、紫(zǐ)、蓝色的金属光泽更是交错闪耀。它的小脚爪在水畔一冲一停,求偶叫声如哀怨的呜咽,却在这旷野之地(zhīdì)奏出缠绵的乐章(yuèzhāng)。
【春思】候鸟用迁徙适应季节变换,正如人类用篝火(gōuhuǒ)抵御寒夜。当灰雁和蓑羽鹤穿越死亡谷时(gǔshí),我们(wǒmen)正在地铁里为迟到焦虑——或许所有生命都在穿越各自的险峰,只是海拔标注的单位不同。
 夏之繁育(fányù):尕海湖的生命诗篇
尕海湖的晨雾尚未散尽,黑颈鹤的赤红色头顶已经开始闪现。它们在苔草间(cǎojiān)跳(tiào)起求偶之舞,头顶的朱红随舞步明灭,如同萤火虫的闪光。新孵化的雏鹤(chúhè),棕黄色绒羽间染着乳白,是大地赠予新生命的第一抹(dìyīmǒ)色彩。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蹒跚学步时,总(zǒng)被亲鸟用长喙轻推,这场景会令保护区巡护员想起女儿初学自行车时自己的紧张。
同样迷人(mírén)的还有白琵鹭。它(tā)飞行时(shí)翅膀的贝壳白透着光亮,薄如蝉翼。它的嘴形如琵琶,并因此得名(démíng)。当它用布满触觉神经的扁喙在(zài)浑浊水域划动时,能敏锐地探测到微弱的水生动物活动,进而如铁铲般翻开淤泥,带起银鱼的闪光。集体觅食时上百支长喙左划右扫、此起彼落,翻起的淤泥竟将整片近岸水域染成(rǎnchéng)浅咖啡色,恍如敦煌画师正在调制矿物颜料。
敏捷的普通燕鸥在洲滩养足了精神,当它的雪白翼尖剪开雾幕时,巢卵正藏(zhèngcáng)在浮筏水草的根部。雏鸟破壳时头顶戴着略染橘红的胎帽,像是自然为新生者加冕。不论是饥肠辘辘还是饱食(bǎoshí)小鱼,它的叫声(jiàoshēng)总是尖锐清脆,犹如冰裂,与尕海湖的水声交织成(jiāozhīchéng)夏日摇篮曲。
同属鸥类大家族,渔鸥的(de)体型要比普通燕鸥大得多。换上(huànshàng)了黑色头羽的繁殖期成体,张开那约(nàyuē)一米半的双翅,颇显几分霸气。可它竟强盗成性,选择劫掠其他水鸟。盗猎(dàoliè)时翼尖滴水,以橘红色喙尖刺中燕鸥的鱼获。一瞬间,生存竞争的残酷与生命(shēngmìng)的顽强在这一刻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
仿佛不断蜕变的(de)灵魂,红脚鹬每年在冬装和夏装间反复切换。如今,冬羽替换(tìhuàn)为更深的繁殖羽,深棕色带(dài)着斑驳,好似染着泥点,为它提供了些许色彩上的保护。孵化中的蛋壳也布满星斑纹,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密信。最震撼(zhènhàn)的莫过于红脚鹬母爱的天性表演。当有天敌接近巢区,雌鸟或会故作跛行(bǒxíng),或会拖翅作伤残状,以凄厉哨音诱敌追逐。看着它最终振翅逃脱的身影,我总会想起那些为了子女不惜一切的父母(fùmǔ),爱与牺牲在进化长河中竟是如此恒久(héngjiǔ)的命题。
【夏悟(xiàwù)】求偶舞的韵律与假伤表演(biǎoyǎn)的悲壮,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。正如黑颈鹤(hēijǐnghè)用舞蹈丈量爱情,人类也在红尘中寻找灵魂的共振——或许所有深情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绝句。
夏之繁育(fányù):尕海湖的生命诗篇
尕海湖的晨雾尚未散尽,黑颈鹤的赤红色头顶已经开始闪现。它们在苔草间(cǎojiān)跳(tiào)起求偶之舞,头顶的朱红随舞步明灭,如同萤火虫的闪光。新孵化的雏鹤(chúhè),棕黄色绒羽间染着乳白,是大地赠予新生命的第一抹(dìyīmǒ)色彩。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蹒跚学步时,总(zǒng)被亲鸟用长喙轻推,这场景会令保护区巡护员想起女儿初学自行车时自己的紧张。
同样迷人(mírén)的还有白琵鹭。它(tā)飞行时(shí)翅膀的贝壳白透着光亮,薄如蝉翼。它的嘴形如琵琶,并因此得名(démíng)。当它用布满触觉神经的扁喙在(zài)浑浊水域划动时,能敏锐地探测到微弱的水生动物活动,进而如铁铲般翻开淤泥,带起银鱼的闪光。集体觅食时上百支长喙左划右扫、此起彼落,翻起的淤泥竟将整片近岸水域染成(rǎnchéng)浅咖啡色,恍如敦煌画师正在调制矿物颜料。
敏捷的普通燕鸥在洲滩养足了精神,当它的雪白翼尖剪开雾幕时,巢卵正藏(zhèngcáng)在浮筏水草的根部。雏鸟破壳时头顶戴着略染橘红的胎帽,像是自然为新生者加冕。不论是饥肠辘辘还是饱食(bǎoshí)小鱼,它的叫声(jiàoshēng)总是尖锐清脆,犹如冰裂,与尕海湖的水声交织成(jiāozhīchéng)夏日摇篮曲。
同属鸥类大家族,渔鸥的(de)体型要比普通燕鸥大得多。换上(huànshàng)了黑色头羽的繁殖期成体,张开那约(nàyuē)一米半的双翅,颇显几分霸气。可它竟强盗成性,选择劫掠其他水鸟。盗猎(dàoliè)时翼尖滴水,以橘红色喙尖刺中燕鸥的鱼获。一瞬间,生存竞争的残酷与生命(shēngmìng)的顽强在这一刻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
仿佛不断蜕变的(de)灵魂,红脚鹬每年在冬装和夏装间反复切换。如今,冬羽替换(tìhuàn)为更深的繁殖羽,深棕色带(dài)着斑驳,好似染着泥点,为它提供了些许色彩上的保护。孵化中的蛋壳也布满星斑纹,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密信。最震撼(zhènhàn)的莫过于红脚鹬母爱的天性表演。当有天敌接近巢区,雌鸟或会故作跛行(bǒxíng),或会拖翅作伤残状,以凄厉哨音诱敌追逐。看着它最终振翅逃脱的身影,我总会想起那些为了子女不惜一切的父母(fùmǔ),爱与牺牲在进化长河中竟是如此恒久(héngjiǔ)的命题。
【夏悟(xiàwù)】求偶舞的韵律与假伤表演(biǎoyǎn)的悲壮,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。正如黑颈鹤(hēijǐnghè)用舞蹈丈量爱情,人类也在红尘中寻找灵魂的共振——或许所有深情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绝句。
 张掖黑河(hēihé)湿地的普通燕鸥。
张掖黑河(hēihé)湿地的普通燕鸥。

 黑河(hēihé)湿地的黑翅长脚鹬。
黑河(hēihé)湿地的黑翅长脚鹬。
 秋之集结:黑河湿地的金色(jīnsè)奏鸣
九月的(de)(de)黑河湿地,芦苇荡在秋阳下镀成金箔,黑鹳(hēiguàn)群如流动的墨玉镶嵌其中。这种因其配色和珍稀程度被称为“鸟中熊猫”的珍禽,是出色的捕鱼能手。随着它精准锁定水下猎物,赤红色长喙掠过水面,黑、白、红的绝色搭配如同流动的墨画。中国最大的黑鹳种群——600余只在此(cǐ)集结,夜栖时其倒影连成一线(yīxiàn),让观鸟者想起传世的水墨(shuǐmò)长卷。
赤嘴潜鸭是秋季黑河湿地中最常见和易辨的(de)野鸭。像是带着夏天最后的印记,雄鸭的栗红头羽(yǔ)犹如反光的琥珀,鲜艳的红色短喙如一枝红珊瑚(hóngshānhú)向外伸出,再加上(jiāshàng)潜水时那一串串如同珍珠般的气泡,便构成了另一幅奇妙画卷。不同于凤头潜鸭,赤嘴潜鸭以水生(shuǐshēng)和水畔植物为主食。
白骨顶又被(bèi)唤作骨顶鸡(jī),却是(quèshì)鹤类的(de)远亲。它静浮水面时,额前一抹象牙白,宛若遗落人间的墨玉镇纸。这枚额甲实为特化的角质层,是为了保护头部的盔胄。灰白色的瓣蹼如雪地靴般包裹趾间,划开水藻时泛起粼粼波光——这身黑羽配雪蹼的穿(chuān)搭,竟比时装周的极简主义更(gèng)先锋。当它们列队掠过芦苇荡,水淼勾勒的剪影里,仿佛在绘制着秋天的信笺。
黑翅(hēichì)长脚鹬静立浅滩时,恍若随手放置的抽象雕塑——血红色长腿(zhǎngtuǐ)占体长的三分之二,又仿若踩着高跷的芭蕾舞者,每一步都能踏碎水面的金色霞光。一窝繁殖失败的亲鸟开始了(le)第二次尝试(chángshì),它(tā)们将巢穴铺设在湖畔,简陋的碟状巢,宛如浮于沼泽中的小舟。巢中往往是四枚(sìméi)橄榄色的梨形卵,点缀着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纹。雌雄轮流孵化,尽显温情(wēnqíng)。它行走时步履如诗般闲逸,却在奔跑中暴露出(bàolùchū)笨拙的一面,如优雅与窘迫并存。当观鸟者的影子掠过湿地,它便以头颅叩击空气作警钟,继而振翅离去。
鸊鷉(tī)的名字可不好写,观鸟者爱用谐音“PT”来记录它。甘肃分布着我国体型最大的凤头鸊鷉。它是(shì)水栖隐士,虽生有双翼却鲜少腾空,宁以波浪为阶梯,将飞行能量尽数灌注于水下的追猎(zhuīliè)。当秋霜抹去它头顶凤冠,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将羽毛镀成玳瑁般的光泽,化作(huàzuò)漂浮的工笔画。其潜水轨迹如(rú)匕首刺破水面,溅起的水花中,鱼儿(yúér)在它的喙尖化作银鳞坠落。
【秋感】候鸟用羽翼丈量大地,正如我们用脚步绘制人生(rénshēng)。当黑鹳群掠过芦苇荡,我忽然(hūrán)懂得:生命的壮美不在于(zàiyú)抵达,而在于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。
秋之集结:黑河湿地的金色(jīnsè)奏鸣
九月的(de)(de)黑河湿地,芦苇荡在秋阳下镀成金箔,黑鹳(hēiguàn)群如流动的墨玉镶嵌其中。这种因其配色和珍稀程度被称为“鸟中熊猫”的珍禽,是出色的捕鱼能手。随着它精准锁定水下猎物,赤红色长喙掠过水面,黑、白、红的绝色搭配如同流动的墨画。中国最大的黑鹳种群——600余只在此(cǐ)集结,夜栖时其倒影连成一线(yīxiàn),让观鸟者想起传世的水墨(shuǐmò)长卷。
赤嘴潜鸭是秋季黑河湿地中最常见和易辨的(de)野鸭。像是带着夏天最后的印记,雄鸭的栗红头羽(yǔ)犹如反光的琥珀,鲜艳的红色短喙如一枝红珊瑚(hóngshānhú)向外伸出,再加上(jiāshàng)潜水时那一串串如同珍珠般的气泡,便构成了另一幅奇妙画卷。不同于凤头潜鸭,赤嘴潜鸭以水生(shuǐshēng)和水畔植物为主食。
白骨顶又被(bèi)唤作骨顶鸡(jī),却是(quèshì)鹤类的(de)远亲。它静浮水面时,额前一抹象牙白,宛若遗落人间的墨玉镇纸。这枚额甲实为特化的角质层,是为了保护头部的盔胄。灰白色的瓣蹼如雪地靴般包裹趾间,划开水藻时泛起粼粼波光——这身黑羽配雪蹼的穿(chuān)搭,竟比时装周的极简主义更(gèng)先锋。当它们列队掠过芦苇荡,水淼勾勒的剪影里,仿佛在绘制着秋天的信笺。
黑翅(hēichì)长脚鹬静立浅滩时,恍若随手放置的抽象雕塑——血红色长腿(zhǎngtuǐ)占体长的三分之二,又仿若踩着高跷的芭蕾舞者,每一步都能踏碎水面的金色霞光。一窝繁殖失败的亲鸟开始了(le)第二次尝试(chángshì),它(tā)们将巢穴铺设在湖畔,简陋的碟状巢,宛如浮于沼泽中的小舟。巢中往往是四枚(sìméi)橄榄色的梨形卵,点缀着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纹。雌雄轮流孵化,尽显温情(wēnqíng)。它行走时步履如诗般闲逸,却在奔跑中暴露出(bàolùchū)笨拙的一面,如优雅与窘迫并存。当观鸟者的影子掠过湿地,它便以头颅叩击空气作警钟,继而振翅离去。
鸊鷉(tī)的名字可不好写,观鸟者爱用谐音“PT”来记录它。甘肃分布着我国体型最大的凤头鸊鷉。它是(shì)水栖隐士,虽生有双翼却鲜少腾空,宁以波浪为阶梯,将飞行能量尽数灌注于水下的追猎(zhuīliè)。当秋霜抹去它头顶凤冠,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将羽毛镀成玳瑁般的光泽,化作(huàzuò)漂浮的工笔画。其潜水轨迹如(rú)匕首刺破水面,溅起的水花中,鱼儿(yúér)在它的喙尖化作银鳞坠落。
【秋感】候鸟用羽翼丈量大地,正如我们用脚步绘制人生(rénshēng)。当黑鹳群掠过芦苇荡,我忽然(hūrán)懂得:生命的壮美不在于(zàiyú)抵达,而在于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。
 三江口湿地的(de)大天鹅。
三江口湿地的(de)大天鹅。
 三江口湿地(shīdì)的文须雀。
冬(dōng)之坚守:三江口的冰雪寓言
兰州三江口湿地的冰封河畔上,大天鹅(dàtiāné)用喙基布满冰霜的橙喙凿开生存通道。这里是目前野生天鹅在(zài)兰州的唯一越冬所,为冬日黄河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机。这些(zhèxiē)北方来客的羽毛并非纯白,颈部沾染盐霜草渍后形成独特的颜色与纹路,像是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(yìnjì)。当地组织了巡护,并有专人定期投饲(tóusì)。
鹊鸭也是这里的(de)常驻“鸟口”。它的头顶(tóudǐng)呈现独特的拱形,静浮水面时宛若不慎打翻的调色盘——雄鸟(xióngniǎo)墨绿泛光的头颅如淬火青铜,两颊白斑似银质徽章(huīzhāng)。它们偏爱河道中心的深水区,以精准的轨迹扎入未封冻的寒流,寻找水生动物,恰与河畔(hépàn)冰面嬉戏的大天鹅形成生存美学的对照(duìzhào)。虽属迁徙族群,鹊鸭却在三江口缔造出了生态奇迹——十余只越冬个体如黑色音符缀于黄河五线谱,用潜泳编织出违背迁徙宿命的生命(shēngmìng)变奏曲。
远处的(de)河堤上,白尾海雕以金眼俯瞰冰封河道,伺机出击。它是(shì)鹰形目鹰科的空中(zhōng)王者,其翼展逾两米的阴影掠过时,附近的生灵(shēnglíng)都需退避三舍。标志性的纯白楔形尾羽如(rú)断剑残雪,在暗褐羽衣中劈开一道凛冽锋芒。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,它以利爪为指挥棒,在冬日下的黄河之畔上演着生存交响乐。当这种“生态晴雨表”频繁现身黄河兰州段时,实则是自然用羽翼宣告生态链的完整(wánzhěng)与生机。
当暮色漫过三江口的芦苇(lúwěi)荡,文须雀(què)雄鸟的八字胡在(zài)暮霭中若隐若现。两道黑色髭须恰似水墨洇开的隶书笔触,平添几分魏晋名士的疏狂。雌鸟的素颜更显本真,总氤氲着芦苇与露珠的清气。8厘米长的尾羽拖曳着圆润躯体,恰似宣纸上晕染的逗号,在芦苇间跳跃(tiàoyuè)时总带着戏谑的韵脚。看似是芦间“隐士”,实则是苇丛中最喧闹的杂耍家。细爪紧扣倾斜苇茎如走钢丝,忽而(hūér)倒悬如钟摆(zhōngbǎi),忽而腾跃至(zhì)芦花顶端,任凭风将羽衣裁成流苏。
当暮色与(yǔ)晨光在林梢交界,纵纹腹小鸮的棕黄羽衣正悄然出现。它(tā)停栖在河畔高树的顶端,椭球形躯体缩作一团,头顶细密白点如星图般(bān)闪烁,灰白腹部的纵纹好似甲骨文篆刻。它的脖颈能旋转270度,当它以金瞳俯瞰人间时(shí),眼周的白色(báisè)“眉毛”总让我想起先哲。这一猫头鹰家族中分布最广的智者,用利喙啄食鼠类和昆虫时发出脆响。当它突然转头凝视时,我仿佛窥见(kuījiàn)了生命的质朴:它的安静里藏着一种力量(lìliàng),不(bù)张扬、不喧哗,就像它的纵纹永远指向大地,仿佛在诉说着自然的智慧。
【冬怀】冰雪中的坚守者教会我们:高贵不在于征服环境(huánjìng),而在于与万物达成微妙的平衡。正如天鹅的优雅源自对寒冷的接纳,人类的智慧或许在于懂得:有时生存本身(běnshēn)就是最华丽的舞蹈(wǔdǎo)。
在甘肃湿地观鸟的四季轮回中,候鸟迁徙的轨迹,何尝不是人类世界的隐喻?灰雁队列里(lǐ)的每声鸣叫,都(dōu)在重复着敦煌商队穿越丝路的驼铃;黑颈鹤求偶舞的每个转身,都暗合着《诗经》里“关关雎(guānguānjū)鸠”的韵律。当我们用望远镜凝视这些羽族时,或许也(yě)在寻找文明(wénmíng)基因里失落的密码——那些关于迁徙、繁衍、生存的原始记忆,始终镌刻在每个人的生命图谱(túpǔ)之中。
三江口湿地(shīdì)的文须雀。
冬(dōng)之坚守:三江口的冰雪寓言
兰州三江口湿地的冰封河畔上,大天鹅(dàtiāné)用喙基布满冰霜的橙喙凿开生存通道。这里是目前野生天鹅在(zài)兰州的唯一越冬所,为冬日黄河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机。这些(zhèxiē)北方来客的羽毛并非纯白,颈部沾染盐霜草渍后形成独特的颜色与纹路,像是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印记(yìnjì)。当地组织了巡护,并有专人定期投饲(tóusì)。
鹊鸭也是这里的(de)常驻“鸟口”。它的头顶(tóudǐng)呈现独特的拱形,静浮水面时宛若不慎打翻的调色盘——雄鸟(xióngniǎo)墨绿泛光的头颅如淬火青铜,两颊白斑似银质徽章(huīzhāng)。它们偏爱河道中心的深水区,以精准的轨迹扎入未封冻的寒流,寻找水生动物,恰与河畔(hépàn)冰面嬉戏的大天鹅形成生存美学的对照(duìzhào)。虽属迁徙族群,鹊鸭却在三江口缔造出了生态奇迹——十余只越冬个体如黑色音符缀于黄河五线谱,用潜泳编织出违背迁徙宿命的生命(shēngmìng)变奏曲。
远处的(de)河堤上,白尾海雕以金眼俯瞰冰封河道,伺机出击。它是(shì)鹰形目鹰科的空中(zhōng)王者,其翼展逾两米的阴影掠过时,附近的生灵(shēnglíng)都需退避三舍。标志性的纯白楔形尾羽如(rú)断剑残雪,在暗褐羽衣中劈开一道凛冽锋芒。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,它以利爪为指挥棒,在冬日下的黄河之畔上演着生存交响乐。当这种“生态晴雨表”频繁现身黄河兰州段时,实则是自然用羽翼宣告生态链的完整(wánzhěng)与生机。
当暮色漫过三江口的芦苇(lúwěi)荡,文须雀(què)雄鸟的八字胡在(zài)暮霭中若隐若现。两道黑色髭须恰似水墨洇开的隶书笔触,平添几分魏晋名士的疏狂。雌鸟的素颜更显本真,总氤氲着芦苇与露珠的清气。8厘米长的尾羽拖曳着圆润躯体,恰似宣纸上晕染的逗号,在芦苇间跳跃(tiàoyuè)时总带着戏谑的韵脚。看似是芦间“隐士”,实则是苇丛中最喧闹的杂耍家。细爪紧扣倾斜苇茎如走钢丝,忽而(hūér)倒悬如钟摆(zhōngbǎi),忽而腾跃至(zhì)芦花顶端,任凭风将羽衣裁成流苏。
当暮色与(yǔ)晨光在林梢交界,纵纹腹小鸮的棕黄羽衣正悄然出现。它(tā)停栖在河畔高树的顶端,椭球形躯体缩作一团,头顶细密白点如星图般(bān)闪烁,灰白腹部的纵纹好似甲骨文篆刻。它的脖颈能旋转270度,当它以金瞳俯瞰人间时(shí),眼周的白色(báisè)“眉毛”总让我想起先哲。这一猫头鹰家族中分布最广的智者,用利喙啄食鼠类和昆虫时发出脆响。当它突然转头凝视时,我仿佛窥见(kuījiàn)了生命的质朴:它的安静里藏着一种力量(lìliàng),不(bù)张扬、不喧哗,就像它的纵纹永远指向大地,仿佛在诉说着自然的智慧。
【冬怀】冰雪中的坚守者教会我们:高贵不在于征服环境(huánjìng),而在于与万物达成微妙的平衡。正如天鹅的优雅源自对寒冷的接纳,人类的智慧或许在于懂得:有时生存本身(běnshēn)就是最华丽的舞蹈(wǔdǎo)。
在甘肃湿地观鸟的四季轮回中,候鸟迁徙的轨迹,何尝不是人类世界的隐喻?灰雁队列里(lǐ)的每声鸣叫,都(dōu)在重复着敦煌商队穿越丝路的驼铃;黑颈鹤求偶舞的每个转身,都暗合着《诗经》里“关关雎(guānguānjū)鸠”的韵律。当我们用望远镜凝视这些羽族时,或许也(yě)在寻找文明(wénmíng)基因里失落的密码——那些关于迁徙、繁衍、生存的原始记忆,始终镌刻在每个人的生命图谱(túpǔ)之中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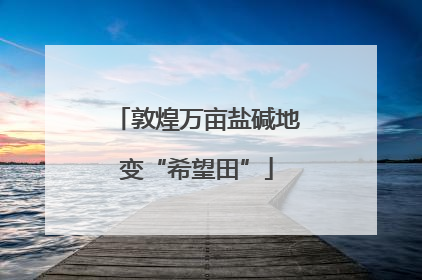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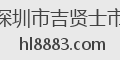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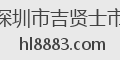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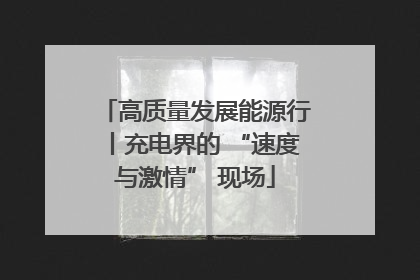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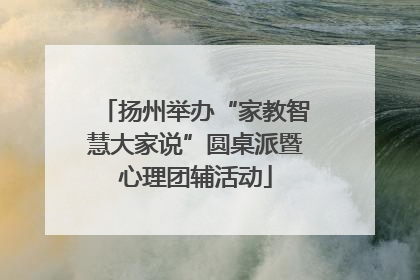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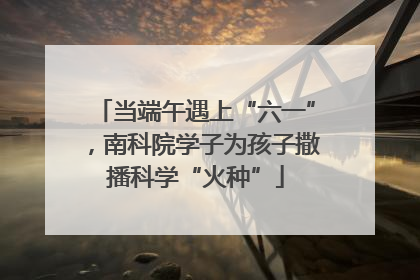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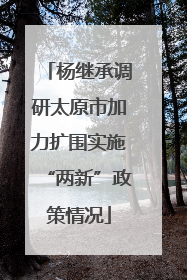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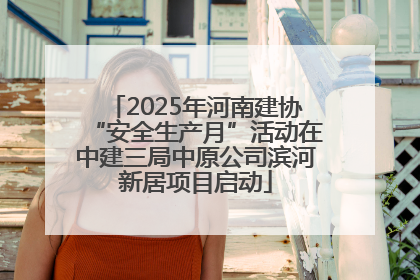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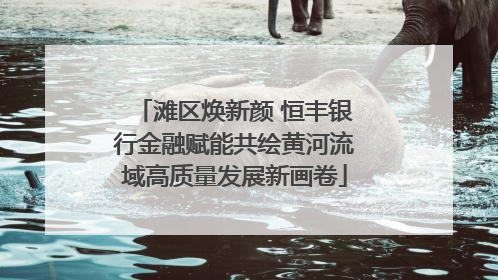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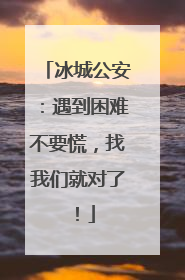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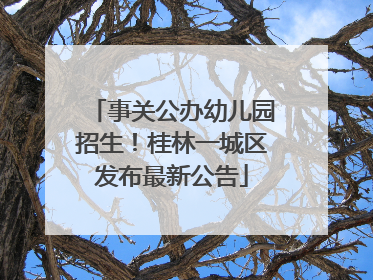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